《糖果男孩》剧情介绍
樱井雪乃(柚木凉香 配音)和樱井奏(生天目仁美 配音)是一对双胞胎,两人自打出生起就从来没有分开过,彼此间的关系之亲密可想而知。如今,升上高中的两人依然享受着充满了平静和幸福的“二人世界”,哪知道,一个名叫神山咲夜(加藤英美里 配音)的女孩子的出现将姐妹两人的日常生活给搅乱了。 奏发现,咲夜似乎和雪乃走得很近,奏误以为两人之间产生了情愫,克制住了内心的失落,奏决定避开雪乃,为他们制造一点私人空间。就这样,一直都是形影不离的姐妹两人渐渐疏远,在此过程中,雪乃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心中深藏的对于奏的感情,一番波折之后,两人终于互相表白了心意,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我的小狗斯齐普坠爱地中海咸鱼翻身迷惑恐怖绘本第五季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心痕如诗朴花英玉熙的电影天台镇死寂亡灵希特勒最后的秘密武器201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重返赌城舞台时光之轮第一季汝之名我在耀瓷小镇等你灵运当铺黄金岁月大牧歌狂暴大蜈蚣洛洛鱿鱼游戏第三季器灵第一季疯狂希莉娅死囚大逃杀2兽拳战队激气连者特别DVDgyungyun!拳圣大运动会异国姻缘新手老卧底第一季千禧曼波
《糖果男孩》长篇影评
1 ) 成年礼&寻枪&寻父&公路片
这一部苗族题材比《我,在贵州等你》更加原汁原味,得天独厚的岜沙苗寨环境+本色出演的本土演员+当地语言,浑然一体的创作诚意十足,让整部电影既接地气,又气质非凡。
成年礼&寻枪&寻父&公路片的设计很有创意,剧本扎实,整体表现也不俗,动人之处比比皆是。
另外,本片对死亡话题的探讨颇具哲学意味,生命树做成棺材的点子第一次见。
2 ) 大美岜沙
惊艳于这样一卷至真至纯至美的苗家少年的故事,任谁也不可能将它讲述完整,不如随了缘,你看就看了,错就错过吧。
托时光网的福参与了导演见面活动,就记录下导演的语言好了。
1首先感谢大家来看这样一部节奏很慢的电影,谢谢大家。
2旅游发现的这么一个地方,本来是苗族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自成一个文化体系,在苗族也是很古老的,这个文化对我是一个触动。
我记得好象张成志在一个散文里写到:肉身置于闹市,灵魂却追逐自然。
对我来说拍这个电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
3我们反映的是苗族的一个文化,这个不是我们演义的也不是虚构的,这也是我个人的一种精神需要。
我觉得房价都长成这样了,我们生活的很不自在,肯定需要一种能让我们平和下来的,让我们觉得自然的,向这种方向我觉得是一种本能吧。
4这个拍摄呢,是一种手工业的方式,内个演员除了旅途上遇到的那些歌手,基本山都是一个寨子里的,就是叫岜沙的这个,我们基本上用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和他们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快成亲戚了。
喝了很多米酒,但是,现在他们也开始喝啤酒了,这个工业化的进程,眼看着就来了。
5我们作为电影的创作者在很坦然很真实地表现苗族这样一个逐渐失去的文化,我们在记录一个正在消失的人类学的文化,我们不觉得这是一种落后,它可能恰恰有它文化上的先进性。
当我们在北京在上海以这样的一种对于居住空间,对于旅行,对于情感,对于交往,这么一个的需求时,我看到在这个寨子里,他们可能比我们的幸福指数要高,他们居住的比我们的房子大,他们推开窗户是云海,他们高兴了就唱歌,他们不高兴了就跳舞,我觉得这是恰恰我们想望的一种境界。
所以我觉得从经济上比较他们也许会落后,这恰恰是我们要思考,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偏离了我们原本的内心多少,而他们的是不是值得我们来思考。
所以说当我们以我们工业化的进度达到今天的时候,他们因为交通等种种原因还在保留着文化的原始性。
在完成了这个之后,有可能是他们在我们的前面,而不一定是我们在有了通讯有了电脑有了宝马车之后就比他们进步。
拍这个电影很重要的一个初衷是我自己想来找我们自己对于生活方式的一个检讨,同时也会发现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恰恰也印证了我们非常值得检讨的一个东西。
6我觉得不管是对于苗族还是对于今天中国,这种文化上的自信是更重要的。
7这个电影融合了几种类型,一个是对文化的记录和表现是遵循当地的文化的我们没有加工,我们想记录到08年我们所能恢复到的文化,假如说是纯粹的记录片来记录的话那也要看记录片的概念了,我觉得把存在的我们今天所能找到的86岁的老人,在这些老人的回忆中,我们把这些文化整和,这也是记录片的方式。
假如从文化意义上讲,那今天的景象和曾经有过的景象是两种真实,我觉得只要没有对文化进行演义和改变,就都是对文化的尊重。
这个电影也可以当作人类学意义上的记录。
8我们拍完到现在已经变化非常大了,在当地对于旅游的过度开发对文化的破坏很大,我们今天也很复杂,它的文化就不再是那种本真的原始的,它是一个非常两难的问题。
9通过一个小孩对他父亲的寻找,更好的能表现他们对自然,对生死,整个他们的文化,以一个少年跨入成人之门变成一个男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截点。
他前一天是少年,第二天就成了一个有责任的男人,所以说我就选了成人礼的时间点。
这也是他们独有的一个文化。
我觉得一个对父亲的寻找更能把我们对精神上的寻找放进去。
在今天我们的世界,我们可能父母都很好很健康,但是我们也要找我们精神上的源头。
寻找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戏剧张力。
3 ) 以图无愧于卑微的人生
两个多月的酗酒和熬夜,终于让睡眠习惯彻底崩溃了,升华到了一种打破时间概念的境界。
比如前天晚上八点多趴在桌子上睡了两个小时,然后碾转到床上,凌晨三点起床,兴致勃勃的做了碗炸酱面。
再比如昨天凌晨一点多睡了,早晨五点多起来后熬了碗白粥。
其实这些都还好,最令人恐惧的莫过于早晨八九点的太阳。
一直以来,这个时间总让我莫名的深深感到绝望。
没有中午的清醒,没有下午的慵懒,没有深夜的宁静。
家里的窗帘都是透光的,无奈翻出两幅弟弟送的蜡染的画挂在窗口,结果太短,仍旧没什么效果。
幸好,一部安静的影片,稀释了这种绝望的气氛。
影片以贵州岜沙苗族为背景,讲述一个苗族少年寻找父亲的一个旅程。
寻找,是一种贯穿人一生的行为,寻找的结果是少年滚拉拉获得了身世的真相。
同时,也在这个旅程获得了少年对生活,对爱情以及亲情的感知,不同的人教会了滚拉拉不同的东西。
也正是这个过程才是滚拉拉真正的成人礼。
而少年贾古旺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寻找,企图融入现代文明的环境,却再《指路歌》的吟唱中回归到祖先那里。
导演没有直接描述古老民族文化和现代社会文明的对撞冲击,而是仅仅在质朴宁静深山生活中氛围穿插了几个县城的画面。
这种方式让人平静的心绪不时被偶尔出来的画面搅乱,也逼迫观众不得不进行思考。
我一直自私认为少数民族都应该成为文化孤岛,以保全历史和文化的痕迹。
可惜现代文明是一把双刃剑,成全了物质,毁灭了意识。
单纯平淡的思维被欲望黑洞所取代。
影片中有些镜头似曾相识,几年前在山里赶路,碰到同样赶路当地人一起坐下来休息。
当地人拿出树叶包着的米饭,水煮白肉和我们分享。
用锋利的小刀割下来的一片片白肉,分明是对现在文明的一种嘲讽,没有味道的白肉却异常好吃。
剧中的岜沙苗族也确实固执的守卫着孤岛,坚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顶部绾着“户棍”,出门身背腰刀、手牵猎狗、肩扛火枪。
可是,这样的守卫,还能坚持多久?
现代文明始终如同猛兽,个体意识被削弱甚至同化不过是迟早的事。
据说少年滚拉拉的扮演者王吉甩也已经剪掉户棍。
很久没有看人文色彩的片儿了,这个类型的片儿越来越少了。
所谓的饕餮大片总是枕头加拳头,这种社会意识和电影工业互相作用的结果最终堆砌出畸形虚幻意识壁垒,让人们争先恐后的进去,却再也逃不出来。
“它除了是一部剧情片,同时也是人类学的一部分珍贵纪录片。
我无力改变世界,只有把握自己的梦想,写在这三千米的胶卷上,以图无愧于卑微的人生。
”正如电影结束后导演所述,至少我们都企图改变过世界,可经过种种残酷的,残忍的,无奈的,于是都扛不住了,于是绝望了。
所谓绝望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
不过,应该有两种“生”。
一种变成顺应,一种演化成旁观。
旁观的人把生活建立个人意识的基础上,构成自己的世界,刻意避免与群体意识发生交集。
看这片的时候还天黑,看完忽然发现天光大亮。
楼下,人们发动汽车,各奔前程。
4 ) 《滚拉拉的枪》:宁静的生活
我非常怀念宁静的生活,就像怀念年轻时候的恋情。
小时候回老家,总是很怀念泥土堆砌的墙壁上的大大的窗户,窗户的后面就是麦田,夏天的风吹过,我能听见麦田里的歌声。
窗户的旁边,有一棵大大的树,从我生下来的时候,这棵树就存在。
下雨的时候,能听见雨水低落在树叶上的声音,放晴的时候,能够看见远山横卧在灿烂的夕阳之中。
夏天,虽然湿热,但是,夜幕降临时的那份宁静却让人感觉到深刻的美,冬天,虽然寒冷,但是,银装素裹的大地却总能让人感觉到庄严的宁静。
我以为,我的一生都将在这里度过......后来,还是离开了那片土地。
无意间看了一部电影《滚拉拉的枪》,很普通的情节,很普通的演绎,尽管我知道,那是一个关于信仰和成长的故事,然而,我还是被电影中的宁静所感动。
我喜欢看那些淳朴的苗族人在蓊蓊郁郁的林中穿行,或剑拔弩张,或温软如玉,或悄声细语,或仰天长叹,每一种姿态都是对生命的崇敬。
寻找:影片想要表达的主题很多,不过宁敬武最聪明的一点就是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来表述自己的观点,这样以来,就让主题更纯粹,更具有说服力。
影片中的滚拉拉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对成长充满了渴望,然而,成长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于是,滚拉拉开始寻找,寻找自己生命中缺席的人。
出乎意料的是,在寻找的过程中,他经历了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情感,至于他如何理解自己的成长,自然是不得而知。
那么,滚拉拉为什么要去寻找呢?
曾经,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有一个圆形,他缺了一个角,很不快乐。
于是,他决定去寻找失落的那一个角。
他向前快速的滚动,唱着这样一首歌谣,“我要去寻找失落的一角,啊哈哈,上路啦,去寻找我那失落的一角。
”有时候,他要忍受日晒,有时候,他要忍受雨淋。
因为他缺了一角,不能滚的很快,所以,他会停下来和小虫说话,或者闻闻花香,尽管这一路非常艰辛,但是他很快乐。
有时候,他也会遇见走失的角,然而,不是太大,就是太小,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合适的角,但是自己却错过了,后来又遇见了合适的角,但是抓的太紧,碎掉了。
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角,让自己成了一个圆。
他本应该很快乐,但是,由于自己成了一个完满的圆,所以跑的很快,不能和小虫聊天,不能闻闻花香,也不能唱歌。
最终,他明白了,于是,他放下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一角,从容的走开。
其实,滚拉拉的寻找不过是一种成长的历程,借助于寻找这个主题来描述一个孩子的成人过程。
他需要的并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问题的答案,他只是希望,在他的生命中,有人能够见证他的成长。
死亡:看了很多电影,总觉得没有死亡的电影是不完美的,在《滚拉拉的枪》这部电影中,导演用非常诗意的方式演绎了苗寨人的死亡。
对树神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
影片中有一出悲剧,尽管是死亡,但是没有给影片增添更多庄严和肃穆,而是让一个孩子通过介入生命流逝的方式来明白成长中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而贾古旺的死亡,可以看出导演对在物欲中寻找生命意义的一种暗示。
从这里我们可以将“死亡”看作是部落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相互碰撞的产物,可以说是一种对现代文明的思考。
相对于都市中的人,我更感慨于那些生于宁静和死于宁静的人,就像苗寨中的人,滚拉拉以及滚拉拉的奶奶,他们一生都保持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因为有信仰,所以他们总是拥有自由,所以他们在任何事情面前都能保持真实和坦然,诚然,他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感谢上天的馈赠。
相比较钢筋水泥城市中的人,这样的生活恍若梦境。
我并不觉得死亡是一件坏事,诚然,人生中的两件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出生和死亡。
在《滚拉拉的枪》这部电影中,我感觉到的死亡是一种背叛故土所付出的代价,自然,这也是一部分成长中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整部电影通过成长这个主题描述了苗族人的文化,不管是演义还是虚构的生活,影片传达出来的是一种真正的宁静。
很多时候,这些部落文化被人以为很落后,其实并不落后,相反,这种娴静的生活以及居住的环境恰好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有时候想,尽管工业化如此发达或将更发达,我依然喜欢原始的文化以及原始的美,那种没有经过修饰的美才最让人惊心动魄。
宁静:或许,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宁静了吧!
很多时候,做选择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你选择了城市的生活,就必须放弃掉宁静的故土,你选择了更好的未来,就必须让自己的灵魂行走于物欲之间。
哀叹宁静的消逝本身是意见略带矫情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宁静本身是可笑的。
我们不能在失去宁静的同时也失去对宁静的向往。
5 ) 本不属于城市
“我无力改变世界,只能把自己的梦想写在三千米的胶卷上,以图无愧卑微的人生。
”影片结尾导演用简单的几句话,说明了自己的理想及对人类文明的尊重。
这是作为艺术家负责任的表现。
影片主要讲述一个叫滚拉拉的16岁的苗族男孩在自己成人礼前寻找父亲送自己一把枪的经典套路,通过这个寻找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理想目标进行精神溯源——对自身生活方式的反思和对幸福的寻求。
全片淳朴,纯真,善良,一个被世俗隔绝也被世俗抛弃的世界。
如此相比我们是多么丑陋。
当然影片描写的世界过于理想,可是对于一个夹杂在凡世间的一个小民族,是否像是我们的淳朴,纯真,善良,早已被功利欲望排挤在内心阴暗的小空间从未释放?
我们是否该去寻找?
小寨的人也想要接触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不属于城市。
贾古旺去广州打工为了一个帽子莽撞的在马路上奔跑因此出路车祸,他还自嘲广州马路太硬。
初次感受城市就接触到了城市的冰冷烦躁与他的世界格格不入。
最后不得以回到家乡,进寨子前他让滚拉拉把他的衣服拿来穿上才进寨子,这是一种简单而庄重的仪式。
他要抛弃污尘回到他的世界,于是他穿上族服回到家躺在床上就安静的离开了,没有伤感。
族人简单的解释就是祖先想他了。
多么简单的解释啊信仰此时成了最大的安慰!
再就是乌巴拉向银行借钱无力偿还躲在山里,并非是他不讲诚信这也说明了他们确实不属于城市,他们的行为方式跟我们不同我们只认钱,这真的很现实乌巴拉不能理解我们的行为方式只有躲进山里。
躲避城市是不得已的选择。
全片让我印象深刻还有山歌,这也是导演侧重表现的也是影片的最终目的。
确实很美```原生态的!
未经雕刻如满山的树一样自然的美
6 ) 相比很多少数民族题材,这个可以了
里面提到行歌坐月,这是侗族男女相恋的习俗。
出现了几首山歌,“你我岁月常相守”最动人。
少数民族风情片,音乐很美,一个穿着传统服饰的少年穿行在城市,是一种别样的感觉。
祖宗传下的规矩,砍柴只能肩挑,为免过度索取,导致山成光头山。
这很环保。
大概越是与自然深入相处的民族,越懂得自然资源的可贵,努力寻求和谐共处。
一个异族少年次成人礼,从男孩到男人的必然之路,寻父和求枪两条线交叉,最终身世之谜揭晓,而奶奶卖掉银饰给孙子做了一把枪,这个很欧·亨利《麦琪的礼物》。
祖孙相拥一刻最动人。
导演宁敬武因本片成名,很多人以为他前途不可限量,大有接班张艺谋等第五代之势,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被高估了,他其实就是一主旋律搞手,本片只不过瞎猫撞着了死老鼠,题材和本子还不错。
7 ) 冲涤心灵的清泉
虽然题材老套、演员业余,但是主题积极向上情感流露自然、风景美丽怡人、表演朴实得体,绝对称得是优雅的并且值得多看几遍的上乘之作。
拉拉的天真纯朴、自尊自强、热心助人的品质在寻父旅程中优雅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在修船匠那里意识到奶奶才是自己的最爱后毅然的回家更是令人畅怀的感动。
完美的成人礼重要,拥有枪的尊严重要,但是自己的亲人才是最最重要的!
此外,小卖部的老板、小女孩、铁匠铺的老板、农夫一家…,这些出现在拉拉旅程中的人都以各种不同的外在但又共同有着善良的内在来感染着我们。
这些善良的人组成的优雅的电影就象一股清泉流过并洗涤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暂时忘却了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尔臾我诈、自私自利、斤斤计较、虚伪假面……
8 ) 关于苗族人的正常生活不是这样的
看着这么高分,进来看了看,首选申明,本人黔东南本地苗族人,导演不是本地人,根本不了解苗族人的风俗,看得恶心,虚假,做作,媚俗,披着苗族的衣装来混弄外人,演员表演生硬,动作表情麻木等等先不说,这个是导演的调度不行,但尼玛的从头到尾那几个演员的口型完全对不上号,现场就是在背台词,配音是后面录进去的,可能是剪辑师不懂苗语吧,但你妈的也不能这样欺骗众生,在大部分人眼里,黔东南山好水好,但是芭莎这个带枪和镰刀剃头的事情是虚假炒作的,89十年代的时候一个摄影师去拍照片,看到本地人在剃头,就喊他们用镰刀比着拍了几张照片,发在杂志和媒体上就火了,政府趁热打铁才吵起来的,搞得当地农民都无心种田了,天天拿着土枪和镰刀表演节目,包括西江,朗德,肇兴,家榜梯田等等一带都是这样的,商业气息恶毒,完全颠覆了苗家人的本质形象,零几年在凯里巴拉河一带到西江,包括兰花村,朗德等等,你只要拿出相机对着老人或小孩咔嚓一下,马上伸手来:"敖块水"(苗语,两块钱的意思),想着都恶心,一起西江没活的时候不收门票,后来有点油水了,只要黔东南身份证都不收票,现在呢?只要是雷山县身份证不收门票,再过几年估计只要不是西江寨上的都要门票了,为什么要把大门搞在下面这么远?要的就是你们每个人出20块钱的车费,不然走路半个小时,中国的旅游业已经发展到了万恶的地步,外地人一来旅游,就什么苗家香苗家甜,几十个苗家姑娘高山流水的灌你酒,你以为那酒不要钱啊,你以为你真的喝了十碗八碗的不会醉,你酒就量好啊?告诉你们,那个不是米酒,是甜酒勾兑的,叫甜酒酿,我们本地人喝那种酒随便十来斤没问题,真正的米酒是苦的,带稻花香的味道,白酒一斤的人,喝八两吹风就倒.要想体验苗族人的热情,还是去那些原始地带,没有被开发,没有被商业污染的地方吧,台江,剑河,榕江等那些边远的地方.不过现在要找那些地方很难了,稍微有点感觉的都被政府搞烂了.
9 ) 经历旅行的寻找,一个真正的成人礼
滚拉拉,为了能有个真正的成人礼而去寻枪,去寻父。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一路上他经历了各种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情感。
在第一个猎人那里,寻枪这个命题就被质疑了,在现代社会中枪的存在远不能在银行的贷款面前保护你,而动物早已不能被猎杀,枪在猎人手里就如同一个摆设,一个符号。
在那收获的家庭中,寻父的目的似乎也变得模糊,如果自己苦苦寻找的父亲也如那男主人一样,那寻父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喜欢一个人和被一个人喜欢总是让人开心的事情,那自己又为何要介入到父亲的新的生活之中呢?
火灾中的人生的无常,仿佛让人觉得一切都变得虚无。
一切飘忽不定,一个家庭在一把火面前是那么脆弱和不堪一击。
一切的意义都在什么地方呢?
最终,滚拉拉在船工师傅那里找到了答案!
枪确实已成为一种符号,而人类的文化正是在无数的符号中传承,就如同祖辈传下来的歌可以将人死后的灵魂带往冥界的家,留着的长发和成人礼上的枪都是滚拉拉能在天地之间找到家的标识。
而当认同了自身的文化后,滚拉拉终于在师傅对没能参加母亲葬礼的终身遗憾中发现,原来自己的心,不在作为符号的枪那里,也不在虚无缥缈的父亲那里。
他的心早已被安放在和她相依为命的奶奶那里。
相对于滚拉拉的旅行,贾古旺的悲剧则可以看成是导演对在物质主义中寻找生活意义的一种隐喻。
片中许多场景反映出文化的冲击,反映出传统聚落对自然的态度,反映出对所谓现代文明的思考。
我在过去几年的学习中,经常往返于传统村落和现代都市之中。
在村落中经常和老人们交谈,了解村落的历史,了解他们的生活。
我并不觉得那些场景被导演刻意的雕饰。
相反那些场景显得相当的真实。
我常感慨于传统聚落中老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他们在天地之间生活的自由,他们在人生无常面前的真实和坦荡,他们获得时的感恩和知足。
相比之下城市生活的物欲横流不正折磨着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么?
我想,我们这些在物欲横流社会中生活城市的人都需要补上如滚拉拉一样的寻找之旅来作为我们的成人礼,让我们思考我们的心是在何处安放。
10 ) 滚拉拉的枪
滚拉拉的枪2015-04-03最开始看这部电影还是由于马原老师老石的推荐,看片名很有意思,于是决定看。
在累成汪的周末。
贯穿整个片子的两条线,一是滚拉拉,这个苗族的15岁男孩,寻找父亲,寻找枪的历程。
二是一路上展现的苗族的山水、风情、风俗。
先说后一点,对苗族并不了解,但是这部片子可以说对苗族人的精神世界有一个精致、温和的刻画,不能排除导演为了表现而刻意突出某些情节的意义所在,比如女孩对初次见面的男子敬酒唱情歌,先抛开电影的处理技巧,来谈谈他聊了什么。
电影主题聚焦在枪上,15岁的男子在行成人礼的仪式上,要有一把自己的枪,鸣枪以示成年。
这代表他将成为一个男子汉。
但是父亲出走,母亲早逝的滚拉拉和奶奶相依为命,没有钱买一把枪。
铁匠告诉滚拉拉,可以为他打7折,但是不能不收,不能坏了“祖宗的规矩”。
滚拉拉踏上了寻父之旅,不仅是为了父亲送给自己一把枪,代表着成年、责任、成熟、坚毅的一把枪;也是为了寻找自己命之所源。
每个人问滚拉拉,你要去哪里。
去找父亲。
你知道你父亲在哪里吗。
不知道,所以要去找。
或许可以这样解读,不知道父亲在哪里,所以要去寻找。
不知道生命之源在哪里,所以要去寻找。
不知道成长之路在何方,所以要上路。
所以有一句歌词在唱滚拉拉,“哥从哪里来,哥到哪里去”遇见的第一个人,是孤独的猎人。
因为欠银行贷款而躲在山里,有一个有名的猎人父亲。
猎人说,现在枪已经没用了,原本用来猎杀动物保护自我的枪,现在只是一个符号和象征,那么滚拉拉是否还那么需要他。
第二次遇见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滚拉拉开始想,人可以同时爱上两个人吗。
阿叔有幸福的家庭,可是夜晚他会牵着另外一个女人的手唱飞歌,流泪。
阿娘说,等你长大就会明白了,有喜欢的人和被人喜欢着,都是幸福的。
第三次滚拉拉遇见了一群火灾中逃出来的人,眼看着自己的家园毁于大火,滚拉拉感受到了生活之无常、生命之无力。
直到他重新上路,遇见了修船工,唱悼词的人。
苗族人死后,他们是回到天那里去了。
上天需要他们,他们也是走在回家的路上。
滚拉拉学会了唱悼词,他开始想念自己的奶奶,于是决定回家了,不再寻找了,“如果一个人不回来了,就是他走丢了,那就不会再回来了”。
电影还想要探讨的一个话题,我想是现代化和少数民族生存境况的冲突。
扩展一下,他可以是多数和少数的冲突,“文明”和“落后”的冲突,不同的生存观和自然观的冲突。
好几个情节都在展现,苗族人是如何思考人和天,和地,和自然的关系。
滚拉拉拿了推车去卖柴,被长辈呵斥,“柴只要够烧火做饭就够了,背柴的时候肩膀疼,难道砍树的时候树就不疼吗。
即使急要钱也不可以。
”他们的观念里,带着对人性贪婪的警惕,为了防止这样的贪婪蔓延,他们宁可让自己过得不那么舒坦,也要遵守“祖宗的规矩。
”最后的底线。
拉拉去卖柴的时候,老板说卖不出不要那么快拿来,最近的价钱也要减掉一块。
拉拉没有还口的力量,只能默认。
在城市生活里面,他们是多么的被动。
拉拉的童年伙伴去了城市打工,他向往卡拉ok后面的城市的生活。
但是因为“户棍”而被拒绝当保安,后来在快餐店当送货员,当掩饰“户棍”的帽子飞出车外的时候,他纵身去捡,头部受伤,回到家的第二天,就再也没有醒来。
帽子成为他掩盖“户棍”和之后的伤口的双重道具,其中又有多少年轻人生活的纠结和痛苦。
双重文化在自己的心里呼喊,传统的苗族的教育铸就了他们灵魂的基底,但外面的世界变化发展又何其大,何其有诱惑力。
电影兼具了记录片和电影的特质,用一个故事冷静和缓地为表达这样一种多数和少数,文明和野蛮的思考。
或许这些村民不是合格的演员,但也因为这样电影有了纯正自然的聚落气息。
到底什么样的文化是“文明”的,或者说文明本身就兼具了野蛮的气质和逻辑?
影片在最后向我们暗示了,苗族的文化是有生命力的,它还有那么多坚守他的人。
虽然包含的民族元素很多,这也是让人觉得意味深长的地方,但比较遗憾的是,影片站立的视角,还是一个外族人的视角,且有一些标签化的嫌疑,一些细节或许还值得考证。
不过这些都无法阻碍我对苗族飞歌的喜爱。
懂的歌唱的民族真是别样温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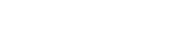




















爸妈在看的~
实拍,现场录音,道具极其简朴,摄影好像用的手机一样,演员演技也一般,但拍范公,多给一星。看着看着倒觉得很质朴,哈哈。
没想到这小成本制作的群演剧看得我眼花缭乱,哈哈,冲着范仲淹去的,还不错,主要是摄像太拉跨。
拍得比较烂